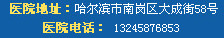实用性与趣味性兼顾、“飞白书”本是宫殿题署之体,其初是为适于实用之目的。由于字径比较大,再加上“白”的辅饰,自然徒增题署应用的视觉效果。蔡邕首创飞白后,诸多大家也参与到“飞白书”的实践的行列,“(飞白书)汉末魏初,并以题署宫阁,后有张敬礼者,隐居好学,独师邕,遂备极其妙。”“(飞白书)汉末魏初,并以题署宫阙,其后有张敬礼、王逸少、子敬并称妙绝。”同时,由于表现“白”的过程极具趣味性,所以帝王贵族选择以“飞白书”作为消磨时间和娱乐的绝佳方式。《书苑菁华》:“召三品以上,赐宴于玄武门,太宗操笔作‘飞白书’,众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竟取,散骑常侍刘洎登御床引手然后得之,其不得者,咸称洎登御床罪当死,请以付法,太宗笑曰:‘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试想,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如果不是帝王因好“飞白”之趣,何至忘却君臣之礼,亦不会产生帝王与臣子如此嬉闹之情景。又如:“文皇帝讳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善飞白书,时于宫中戏为之。”“晋阳公主(太宗女)字明达,幼字兕(音:四)子,文德皇后所生,主临帝飞白书,下不能辨。”等,都反映“飞白书”风靡一时。有时,帝王还会将自己所作的“飞白书”赐予臣子,作为嘉奖之物。史上有诸多有关唐、宋帝王赐字于臣的记录,如:“(张观)平生书必为楷字,无一行草,如其为人,仁宗飞白书“清”字赐观,以赏其节。”“宋太宗赐“秘阁”二字于李至、赐“玉堂之署”四字于苏易;仁宗赐“博学”于张锡、赐“文儒”于张方平等等。帝王赐字的真实原因不可尽数,趣味性仍是其中最为主要的,当然,从《雍熈赐宰臣飞白书》所载来看,帝王在娱乐的同时,递善、矜能、饰伪的成分也可能存在:雍熈三年十月丙申朔,上出飞白书一轴,赐宰臣李昉等,曰:“朕退朝之暇,未尝虚度光阴,观书之外,尝留意于真、草,近又学飞白书,此虽非帝王事业,然不犹愈于游畋声乐乎?”昉等顿首谢。但是,“飞白书”因其趣味性而日益风靡的同时,“飞白书”的实际书写反而越发远离蔡邕始创飞白之初的面目。为了趣味,各种笔具也加入到飞白的书写行列,使飞白偏离原本用毫笔书写的丝丝露白,从而变成“乍浓乍轻”的节节露白、段段露白,显然,这种趣味性自滋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预示着“飞白书”走向消亡、归于沉寂的宿命。“飞白书”宜大不宜小“八分”是在书体创变的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一种特殊形态,而“飞白”又是在“八分”的基础上创法的一种书体样式,其吸收消融了隶书的用笔,王隐、王愔所说的“变楷制”即是指此。《稗编》云:“飞白者,后汉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隐、王愔并云:‘飞白,变楷制也’本是宫殿题署,势既径丈,字宜轻微不满,名为‘飞白’,王僧虔云:‘飞白,八分之轻者。’”由是可见,“飞白书”不仅变楷制,而且是字径比较大、适合题署之用,另外再加上“白”与“黑”的节奏对比,显然使题署之大字又平添了几许活泼与生动。书写实践和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要想在较小的字构、很短的线条上表现这种“白”,显然是无法充分展现“飞白”之美的,这似乎和黄庭坚的个性笔法亦有相通之处,其必须借助长线条来表现,这也是黄庭坚的个性笔法呈现长枪大戟之貌的原因所在,因此“飞白书”更适宜写大字而不宜写小字。顺便提及一点,虽然“飞白书”创法于八分,但“飞白书”毕竟不是八分,所以,八分的生变,同样是“因事”之需,以适应变化的社会需求,从而解散篆体融入更轻快的书写节奏,故八分有“简略赴急疾之用”之说,但不能推演飞白亦有奔赴急疾之用的特点。“飞白”只是在母体的体势上借力于八分,而要想表现出“飞白书”的“白”,是不可能在急疾之间完成的,因此,《飞白之美》一文关于“飞白书”特点及其魅力中说“飞白书可作奔赴疾趋之用”是没有依据的,所引《书断》中关于蔡邕所说草书为避篆隶之难而救急之说的论据似与论点亦毫无联系。飞白本为难工,何来救急?《墨池编》载太宗所云:“飞白字势罕工,吾亦恐自此废绝矣。”所言亦指此。因此,“飞白书”不仅不可急就,反而是需耗费较其它书体更多的时间,这种难工的“丝丝露白”再加上超大的字径,决定了飞白不可能有赴急疾之用的特点。飞白“用笔”之特殊性飞白“用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用笔材质,二是用笔方式。毫无疑问,对于飞白这一特殊书体样式,其用笔有自身的一定独特性和重要性。《飞白书论集成》一著中论道:“笔于飞白,关系重要,不得其笔,不仅减少书之美观,且易流于江湖一派,而大影响于书之价值”由于蔡邕是从役人用垩帚成字而悟得飞白之法的,所以师飞白之法者,不乏用近于帚之形质工具的,唐太宗即是其一。另外,虞和《论书表》云:“子敬出戏,见北馆新泥垩壁白净,子敬取帚沾泥汁书方丈一字,观者如市,羲之见叹美,问所作,答云‘七郎’,羲之作书与亲故云:‘子敬飞白大有意’,是因于此壁也。”由此,笔者不由想起孩提时期所见到的大字标语,其中仿宋、黑体美术字、楷书、隶书最为普遍,书写者所用工具就是粉刷石灰墙的鬃帚,即所谓之“垩帚”,偶有写得过于急促者,或帚中石灰水不足时,仿佛有得飞白之遗韵处。然切不可以此为凭,认为飞白即为帚或近帚的材质工具所书。作为一个为世所重的书法名流,献之见“垩壁白净”,不经意间想到蔡邕见役人垩帚成字之说,一时起兴,戏玩遣怀完全有其可能,若以此来说明“飞白书”之工具,却不足为据。对此,黄伯思有一段精彩论述:唐太宗飞白,皆用相思为片板,若髹刷,然以书殊不用豪笔,故作字无浓淡纤壮之变,非古也。当蔡邕于鸿都下见工人以垩帚成字,归而为飞白之书,非便用垩帚,盖用笔效之而已。今人便谓所用木笔为垩帚,谬矣!除了木质以外,还有用皮、竹等其它材质的笔。“今之飞白书者,多以竹笔,尤不佳。宜相思树制其末,而漆其柄,可随字大小作五七枝妙,往往一笔书一字,满一八尺屏风者。”很显然,这与飞白最初形态是有很大距离的,以至于飞白终被堕入误解之境,也是必然。《六研斋笔记》即云:“元人好写飞白石、飞白竹,缥缈天成之态亦可想见,若以勾白竹指为飞白,则失之远矣。”同样是指对飞白书产生的效果认识上的不足。关于飞白之“用笔”和飞白书的最初形态,黄伯思的“非便用垩帚,盖用笔效之而已”是非常重要的启示。“飞白”最实用、常用之笔即为“豪笔”,“豪”通“毫”,只有用“豪笔”才能得到“轻若丝发”“重若云山”“浓淡相错”的视觉形象,用其它材质很显然无法达到这种视觉效果。鲍照飞白用豪笔乃能成字,或轻或重也。盖或轻若丝发,或重若云山,浓淡相错乃成字。若不用豪笔书之,则不能若此。今观十体中,飞龙二字作“飞白书”,正用豪笔作,与散隶颇相近,但増缥缈萦举之势。欧阳率更亦云:‘萧侍中飞白轻浓得中,如蝉翼掩素,其为前贤所重如此,嗟乎!这种“轻浓得中”、“蝉翼掩素”之状的笔画效果,恐怕用木、竹、皮、毡等材具很难达到。《法书要录》又云:子云书笔迹健瘦,萦丝索铁。昔传子云作笔而心用胎发(按:《江宁府志》云:南朝有姥善作笔,萧子云常用之,笔芯用胎发),故纤细不失。由是可知,萧子云常用胎发毫笔,另又知萧子云创造出“雅合帝意”“意趣飘然”的小篆飞白,至于萧子云的飞白篆是否即为胎发软毫所为,不得而知。但以毫笔作飞白是可以肯定的,其它所有材质之笔,都是对“飞白书”古法的误解或初级模仿,李甸春在《飞白书论集成》中,结合其自身的实践体会,又论道:由此可见,作飞白书,当以豪笔所书者为上乘。盖利用其富于弹性,“可轻可重”以作“浓淡纤壮之变”也。余做是书,始终不易豪笔者,即以此耳。”又:故豪笔者即普通所用之毛笔也。但以适用言,以颖短而毫软硬者(笔者按:当为兼毫)为宜,如能定制,则更善矣。以余所经,作楹帖以鸡狼为最宜,紫毫次之;榜书则应改用六开猪毫。普通的毛笔是圆锥的形状,其便于使转翻折、八面用锋。而要想表现出“飞白书”的视觉效果,则需要不一样的用笔发力方式,笔者个人的体会是:用笔多近于隶书波画之法。这就需要用笔时发力调按,使毫铺开,锋成扁状,方能书就。因此,特殊的用笔方式是“飞白书”的属性之一。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zz/6850.html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zz/68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