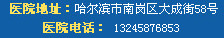在不涉及友人知己,只表达个人心志时,白石的文字便如凌寒傲放的冬梅般,是艳的,也是冷的。
世人评白石词,道是“才子之词”,“幽韵冷香”,“在乐则琴,在花则梅”,“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不一而足,却都不如白石自己在《念奴娇》中写下的这一句“冷香飞上诗句”,既有无限诗情,又恰切绝妙。
闹红一舸,记来时、尝与鸳鸯为侣。三十六陂人未到,水佩风裳无数。翠叶吹凉,玉容销酒,更洒菰蒲雨。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
日暮青盖亭亭,情人不见,争忍凌波去。只恐舞衣寒易落,愁入西风南浦。高柳垂阴,老鱼吹浪,留我花间住。田田多少,几回沙际归路。
——姜夔《念奴娇》
这种冷,似是入了骨,那些飞上诗句的冷香,不是浪一般汹涌而来,也并非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它在空气里是一缕细线,缠缠绕绕勾人心魄;在河海里是一涓细流,安静低调兀自流淌;在人世风情里是一弯遥远锐利的新月,冷冷清清挂在天际,教人于不经意间撞见了,虽不一定赞叹,却一定有惊艳。
他的文字,还像是一张古琴,琴身上有流水断纹,久经年月的样子,琴音透澈宽润,基调却仍是冷的,似从天上传来,在天地之间的辽阔大气中,翩翩而下,洗净凡俗世人沾染浮华的耳朵;又似隐士于一方与世隔绝的孤岛上随心奏出几个音符,有不求知音赏的清绝,也有欲说还休的寂寞。
这种文字之美,不是一览无遗的,需要绕几个弯,才能与它惊喜相逢。一如白石其人,不了解他的人说他清高做作,了解他的人才知他其实是艳极成灰,燃烧尽了,才有如此冰冷寒绝。
居湖州期间,姜夔曾卜居弁山白石洞下,有一位名叫潘柽的友人戏称他为“白石道人”,姜夔答以诗云:
南山仙人何所食,夜夜山中煮白石。
世人唤作白石仙,一生费齿不费钱。
许是觉得“白石道人”这个名号与自己性情颇合,姜夔对此欣然领受,此后他的曲词集便皆以“白石”命名。
“白石”二字,有一股清清冷冷、脱去烟火气息的洁净感,于姜夔、于他的词笔再适宜不过。便如清澈溪流里躺在水底的一块苍白静默的石子,任水面上多少时光汩汩流过,它只在自己的世界里自成一统,执守那一片无法被侵入、被污染的领域;又如冰天雪地里的一幅画,没有一丝血肉的活气,是禅语“银碗里盛雪”,自有高绝凛冽的风姿,又有清坚默然的底子;更若重笔勾勒的一枝旁逸斜出的梅枝,是瘦的、硬的、浓的,却也是空的、淡的,只一径指向虚无里去。
这首咏西湖荷花的词,最能彰显白石词风。
虽然白石自淳熙十四年(年)起已定居湖州,但他自己一直没有停止奔波。有一段时间白石寓居武陵,往来于临安、吴兴等地。在武陵期间,他常与二三好友泛舟游玩。古城野水边,乔木参天,水中荷花亭亭,意象之幽深闲静,简直不似人间。到了秋季,水流枯竭,硕大的荷叶出水耸立,竟达寻丈。白石与友人列坐其下,抬头唯见一片碧绿,遮天蔽日,清风徐来之时,荷叶连连,疏疏摇动,间或窥见一艘游人画船驶过,实在惬意至极。
后来他游西湖,才知西湖荷景,另有一番风味。如果说武陵荷花是阔远风景里的一抹疏宕,那么西湖荷花便是碧青湖波上绯红花色,相映生姿,是江南烟雨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佳人,还是盛景里的超尘拔俗,旖旎中的雅洁,浓墨重彩里的淡远清净。
《念奴娇》词,通篇写荷,却无一句提及“荷”字,这是白石咏物时极爱用的一种手法。他是不肯说直白了,怕寡淡无味;亦不肯道尽,怕不留余地;更不愿束缚住词笔,束缚品词之人的想象,怕落了前人俗套,也怕掉进自己的窠臼。
他是写一首词也要用心良苦的人,及至词写出来,却又不见用力痕迹。奇思妙想,奇词妙句,全似浑然天成,神来之笔,仿佛从天上流云里随意裁剪一片,从万花丛中任意摘取一朵,牵一缕清风,蘸一点月色,便可成诗。
那一日,他仿佛误入了荷花深处,美景扑面而来,他于其间只是无声。游艇无声划过,荡开密密荷叶、盛放荷花,路过对对戏水鸳鸯,生怕惊动了这花鸟相悦的好景。如南唐小周后夜间去会李后主,手提金缕鞋,也是怕惊动。不惊动,其实是情意。白石面对西湖荷花,无声而过,也是用了情,不是浮华轻佻,而是庄重。他悄悄地来,一直到了人迹罕至之处,才终于放下心来,专心赏花。这时,他眼中的荷花竟以水波为佩带,以清风做衣裳,出水临风,恍若翩翩仙子,仙容宛然。
“水佩风裳”本是唐代“鬼才”李贺赞名妓苏小小之语。他在《苏小小墓》一诗中道“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赞苏小小成了幽魂之后,仍然不减生前绝代风姿。其实,钱塘虽有苏小小墓,关于她的生平也颇多传言,苏小小其人却很可能是出于时人杜撰。想来,这位传说中的美人,其风神姿容亦是后人想象而来,故而以“风为裳,水为佩”来形容她,实在再恰当不过。白石挪用此佳句写西湖荷花,遐想间,花出污泥而不染,有脱俗风度,人亦似从画里走出来,缥缈若神,仿佛下一秒就要脱逸而去,人与花,真是相映生辉。
少顷,菰草蒲叶间,洒下点滴细雨,翠绿荷叶间吹来凉爽清风,绯红荷花被细雨点染,好似佳人醉酒面容,此情此景,沁人心脾。分明是白石因此诗兴大发,挥笔写就这首《念奴娇》,他却偏道是清风细雨间,微醉的荷花嫣然一笑,倩影摇动,飞进了他的诗篇。待日暮苍茫时,他甚至设想这些亭亭玉立的出水芙蓉是在等待情人,苦等不至,却也不忍就此凌波而去。实则不忍离去的哪里是荷花,明明是白石自己。他是对这如佳人般美好醉人的荷花,起了怜香惜玉之心。
所以他开始有了担忧,怕那犹如舞衣的荷叶天寒易落,自己只能站在西风吹彻的水滨与它依依告别,任离愁蔓延侵袭。而此时此刻,荷花正艳,荷叶正碧,湖岸高柳垂阴,湖中老鱼吹浪,皆在殷勤挽留,他确是不舍离去,怕离去后美景不再。
面对这一方西湖胜景,白石动了心,也用了情。只因荷花之高洁幽冷,正是他心头所喜。他爱荷花之冷香,爱荷之绝俗风姿,亦是自爱。他对荷花用情,赞它真情不渝的品节风范,亦是以之自诩。一如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爱莲说》中所言:“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
白石其人,正如这般写照。
他不是汲汲于富贵之人,也终究不能如陶渊明般抛下尘俗,隐逸终生,他是入世之时,有出世风度,出世之际,又有入世分寸。他是如莲般的君子,沉浮于江湖苦雨,却始终保持清旷襟怀,高雅情操,与众多高官贵胄交往,却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耿介自持,可谓“出淤泥而不染”;他一生都如孤云野鹤,超俗拔尘,却始终重情重义,于友情能插刀于两肋,于爱情则真心以待,专一不渝,可谓“濯清涟而不妖”;他想求功名便靠自己的能力去求,想要爱情便用自己的方式去争取,即便终生一无所成,也并不攀附他人,只是永远笔直洁净地站立,让才情和品性淡淡散发馨香,可谓“远观而不可亵玩”。
单看白石词笔,冷香幽逸,便知他的君子之风。在动荡江湖里越是尝尽飘零之苦,一事无成之痛,生离死别之殇,他越是要在词里隔绝尘世的凄风苦雨,将每一句词都作得离地三寸,作得飞扬高蹈,仿佛不如此,就无法留住自己的孤绝骄傲。这些清冷的词,好似为他阻挡人世流年、尘俗烟火、生命悲欢的一堵高墙,又似一座琉璃顶、白玉壁的天上宫殿,当他即将在凄风苦雨里熬白了头时,也仍能供他怀想往昔的青春年少,供他坐在空空四壁中央,垂怜自己一生的孤独和凄寒。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yf/79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