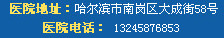北京市治疗白癜风专科医院 https://m.39.net/pf/bdfyy/xwdt/〔四二〕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译:古今词人在格调上,没有比姜夔更高的,可惜他不在意境上下工夫,所以他的词作让人觉得没有言外的余味、弦外的余响,终究不能列入第一流作者。四十二则评析:此则王国维继承了前人论词的方法,重点强调了格调和意境。他借对姜夔词的评判,褒扬了意境(与境界一脉相承),并认为意境高比格调高更加重要,只有意境高的人才称得上是第一流的作者。那什么是格调呢?姜夔本人在《白石道人诗说》有言:“意格欲高,句法欲响,只求工于句、字,亦末矣。故始于意格,成于句、字。句意欲深、欲远,句调欲清、欲古、欲和,是为作者。”从这段话可知所谓“格调”即是意格句调,所谓“格调高”就是用意深远,字句声调清脆和谐。单从格调来讲,姜夔确实是按照他的理论主张创作诗词,王国维也看出了这点,所以对姜夔词的格调给予了很高评价。但王国维为了支持自己提出的“境界说”是最高的评词标准,他必须从“意境”上给予姜夔否定性的评价。针对意境,王国维讲到的“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固然属于意境中的表现,但更接近于“神韵说”的主张。这可以视为王国维提倡的真景物、真感情的“境界说”的一种补充说明。从这里可以看出王国维在提倡“境界说”以求“成一家之言”的同时,也部分接纳和吸收了前人的评词主张。那姜夔的词到底有没有“言外之味,弦外之响”呢?答案是肯定的,并不像王国维讲的那样。姜词重比兴和寄托,辞精意隐,需要了解词中用事(用典)才能体会出他的良苦用心。像《齐天乐·蟋蟀》、《暗香》、《疏影》等作品,乍看过去,古淡朦胧不知所云,细思细想,意味无穷。姜夔又深晓音律,所谓的“弦外之响”更是不成问题。姜夔词之所以被王国维这样评价和看待,最主要原因还是他的个人审美观念决定。他不太喜欢间接、意隐、用典太多的作品,他觉得那样的作品太“隔”。景不真,情不真,不符合他“境界说”的理论主张。〔四三〕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则祖梦窗,以白石、梦窗可学,幼安不可学也。学幼安者,率祖其粗犷滑稽,以其粗犷滑稽处可学,佳处不可学也。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气象论,亦有「傍素波干青云」之概。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拟耶?译:南宋词人中,姜夔有格调而缺少性情,陆游有气象而缺少神韵,其中可以跟北宋词人平分秋色的,只有一个辛弃疾罢了。近人作词亲近南宋而疏远北宋,是因为南宋的词容易学,北宋的词不容易学。学南宋的,不是亲近姜夔,就是亲近吴文英,是因为姜夔、吴文英比较容易学,而辛弃疾不容易学。学辛弃疾的人,都亲近他的粗犷、滑稽,是因为他的粗犷、滑稽比较容易学,而真正好的地方不容易学。辛弃疾词好的地方,在于有性情,有境界。就拿气象来说,也有“横渡白浪,高上青云”的气概。这怎么是后世龌龊的小人所可比拟的呢?四十三则评析:王国维在此则中把前人的多种评词学说都加以使用,有“格调说”、“性灵说”、“气象说”、“神韵说”,其中他重点肯定了自己的“境界说”,但不小心也重点肯定了“性灵说”(性情)。他可能是有意回避使用“性灵”,而用“性情”来替代“性灵”,这样“境界说”更具有理论的唯一性和最高性。王国维此则有多重目的。一是矫正清代词坛以南宋为宗的风气,进一步“抬高”或者说恢复北宋地位。二是通过姜夔、吴文英的易学与辛弃疾的不易学,重点肯定辛弃疾的词学造诣,也否定着清代词坛以姜、吴为宗的主张。三是通过辛弃疾词有性情,有境界,为自己的“境界说”立论。〔四四〕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译:苏轼的词旷达,辛弃疾的词豪放。没有二人的胸襟而学他们的词,就好像东施仿效西施捧心,适得其反。四十四评析:苏轼词旷达和辛弃疾词豪放这不是什么新论,早已是词坛公认的事实,至于二公“胸襟”的说法也是承袭前人。此则是承续上则的“可学”与“不可学”而来,表面强调的是胸襟,实则是强调天赋和才性。学力可以后天学习和培养;而天赋和才性是先天的,不可强求。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wh/8311.html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wh/8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