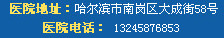禹穴秘境的文化积淀
撰文/赵兴武图片/何发志王清贵老枪
“禹穴”其名,最早见载于《史记》,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说,他考察大禹治水遗迹时,曾经“上会稽,探禹穴”。这六个字很容易被理解为到“会稽”去探访“禹穴”,那么“禹穴”就应该在今浙江绍兴了,但唐代大诗人李白却将“禹穴”二字题写在北川禹穴沟的山崖上。明代学者杨慎通过对李白题字的研究,认为司马迁所“探”的“禹穴”,应该是在北川的禹穴沟。虽然这种说法难以被人理解,但如果考虑到司马迁自述其考察禹迹时曾“西瞻岷山及离堆(都江堰)”,那么他到北川探访“禹穴”,就是完全可能的。自杨慎作出北川“禹穴”是大禹降生地的判断之后,不时有文人墨客前往实地考察,使禹穴沟的崇禹文化得以发扬光大,逐渐形成除石纽山之外北川又一个大禹文化深厚的访古寻幽胜地。
▲禹穴秘境
01
唐代李白“禹穴”题刻
为禹穴秘境奠定人文基调
在北川禹里镇石纽山以北不远的地方,有一道数千米长的峡谷,俗称清泗沟,因沟内的崖壁上有“禹穴”题刻,又被称为禹穴沟。其地两山夹峙,一水中流,绝壁高耸,树几交柯,完全不适合人类从事生产活动,所以一直保持着原始风貌。据明清时期的地方文献记载,这里就是大禹降生的地方。
▲禹穴秘境
大禹本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但有关其诞生在禹穴沟的故事却带有超现实的神秘色彩。其实,神化大禹,并不是在否定大禹的真实存在,而是为了满足人们崇拜伟人的心理需求。在民间传说中,大凡伟人,总和常人不一样,即使是当代伟人,人们在讲述其故事的时候,也免不了要添加一些神秘色彩。几千年前的大禹从投生到出世,更是与众不同:禹母怀孕是因为吞下了石纽山麓泉水中的神珠,禹母怀孕的时间更长达十四个月,禹母的产子方式也是“背剖生禹”。既然从怀孕到生产的过程都非同一般,那么圣母诞禹的地方也应该有些特别。但在现实中,作为“禹生石纽”的石纽山却很普通,与别的山比起来,并没有多少不一样的地方。于是,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禹穴沟,便逐渐成了人们心目中理想的大禹降生地。
▲禹穴沟探秘
大禹生在禹穴沟,最早可能是几千年前当地古羌人的说法,但一直未被外界知晓,直到明代《四川总志》将其记录下来,才得以广泛传播。作为官方文献,《四川总志》把禹穴沟说成是大禹降生地,当然不能仅凭民间传说,还需要找到其他依据。这个被认为可信的依据,就是禹穴沟金锣岩上的“禹穴”石刻,而题写这两个字的,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李白少年时期就勤奋好学,对史书上“禹生石纽”、“禹生西羌”、“禹生广柔县”等记载肯定有所了解。而石泉县不仅属古“西羌”之“广柔县”,县城附近又有石纽山,加上禹里一带浓郁的崇禹风气,更让在此隐居的李白有了感性认识。而禹穴沟的民间传说又让他产生共鸣,在这位极富浪漫激情的诗人看来,圣母生下大禹的地点应该有神秘感,离禹里石纽山仅几公里的禹穴沟古朴幽深,正好符合这个条件。
▲明嘉靖十七年(),禹穴沟“禹穴”石刻被云南大理知府杨仲瑗翻刻在云南清碧溪的山崖上,落款为“广汉李白书”(李白故里江油古属广汉郡),肯定北川禹穴沟的“禹穴”题刻是李白的手迹
▲根据北川禹穴沟拓片翻刻在云南大理清碧溪的“禹穴”石刻,落款为“广汉李白书”
虽然李白一生中从未提起过他曾经题写“禹穴”二字,更未对其含义做过任何解释,但在后人看来,这两个字就是李白对大禹降生地点的判断。后世文人在记录禹穴沟的大禹故事时,都以解读李白留下的“禹穴”石刻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白堪称是禹穴沟大禹文化的开拓者。
02
明代杨慎解读“禹穴”题刻
确认禹穴沟是大禹出生地
李白题写“禹穴”之后,除了本地人知晓,一直未被外界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wh/35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