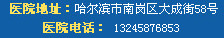《文物世界》年06期
吴承山
宝宁寺水陆画原名“敕赐镇边水陆神帧”,系绢本设色的明代佛教绘画,共计幅,均以细绢为地,用淡红色和黄色花绫装裱,立轴式,除几幅大佛像外,其余均高厘米、宽约60厘米,保存完好,是一套珍贵的明代文物。
水陆画是在佛教寺院内举行佛教仪式———水陆道场(又名水陆法会或水陆斋会)时悬挂的一种宗教画。水陆道场起源于印度,据佛教经籍记载,释迦牟尼弟子阿难尝夜梦恶鬼向其求食,阿难遂设水陆道场,施食救度所有恶鬼。据说,凡被佛法超度过的怨鬼、孤魂,都可以“免罪”、“升天”,故后世盛行不衰。中国最早的水陆道场是南朝梁武帝为他的王妃郗氏所设,后逐渐盛行,自宋代以来流行全国,直至明清,常兴不衰。
伴随着水陆道场逐渐发展起来的“水陆画”,便成为我国宗教绘画中的一个画种。佛教绘画的始创人,据传为三国时期著名的画家曹弗兴,其后许多著名的画家都参与绘制水陆画,例如东晋的顾恺之,唐代的阎立本、吴道子,都是水陆画的高手。但到了五代、两宋山水花鸟画盛行,人物画退居第二位,而道释人物画渐不为文人画家所重,因而大量的寺院壁画均由民间从事绘塑的专业画工来承担。这些画工在画技方面代代相承,上师古人,同时与当代画家相互影响,取长补短。水陆画隋唐以前主要施于寺壁,两宋以后则渐于绢素之上绘成悬挂于壁间的立画,元明以来又逐渐形成单幅立轴,以便于保存、携带。
山西省古代寺庙遗留较多。右玉县地处晋北,兵燹不断,地瘠人苦,宗教文化十分繁盛,可以说村村建庙,人人崇佛。特别是古城右卫,佛道寺庙达百余座,宝宁寺尤其宏大,僧侣众多。过去每逢农历四月初八日(浴佛节)至初十日,寺僧举行水陆道场,悬挂三天,道场结束后便收藏起来。这堂画绝大多数是描写神佛鬼魅、天堂地狱、因果报应的作品,通过艺术形象来感染人,使人易于接受佛教教义,成为宗教的信徒,皈依佛法,谋求解脱。全画记载装帧重裱情况3幅,道释人物幅,各种世俗人物画12幅,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画13幅。各种世俗人物计有帝王、妃、孝子、贤妇、烈女、九流百家等。反映社会生活的有∶雇典奴婢、饥荒饿羿、弃离妻子、枉滥无辜、赴刑都市、兵戈盗贼、军阵伤残、水漂荡灭等。人物画男女老少、正邪美丑,均能表现得恰如其分,生活画形象逼真、气氛浓烈,给人以生活与艺术的感染。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风俗、社会经济状况、服饰、戏剧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那么,这堂画又是从何而来、何时而来呢首先这堂画做工精细,气势恢宏,民间水陆画众多,都难以与其媲美,应为皇宫之物,而且从画名“敕赐”二字亦能说明渊源。右卫民众对其项礼膜拜,视为圣物。由此断定当为明代皇宫之物。
但是这堂画何时“敕赐”右卫之地的呢?史书没有记载,就是地方志《朔平府志》、《大同府志》等也没有陈述其事。而民间盛传有三种版本∶一是清代康熙三十五年(年)玄烨御驾亲征葛尔丹,在右玉被困,而右玉八旗子弟奋力救驾,康熙念其功绩,将此画赏于右玉∶二是明嘉靖三十六年(年),蒙古俺答围困右卫城,右卫军民在外无援兵、内乏粮草的情况下,抵抗蒙古大军八个月之久,嘉靖感念右玉军民勇武,“敕赐”水陆画一堂,用以"镇边",并追念超度阵亡之士的灵魂三是明正统十四年(年)“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敕赐”右玉,以“镇边”祈福。
那么三种版本之言,哪种更接近于史实呢
我们只能顺着历史的脉络加以分析、推断。
康熙赏赐说。康熙亲征葛尔丹,右玉县满汉八旗兵作为西路军的主力在征剿葛尔丹叛军之战中,当推首功。因此,康熙赏赐甚厚,而且由西路军护驾班师,途径右玉而返京。其事《朔平府志》记述甚详∶十二月初七日,驻跸杀虎口九龙湾∶初八日入朔平府城,驻跸费扬古之将军府∶次日宴请有功将士及地方官员乡绅,为清真寺题“古今正教”匾额初十日,至左云十一日至云冈石佛寺,御书“庄严法相”十二日东行回京。并未记载赏赐水陆画之事。《朔平府志》成书于雍正十年(年),距康熙西征不过三十八年,如有帝王赏赐佛画,编撰者应该不会遗漏,恐要大书特书。而且此画于康熙乙酉年和嘉庆十二年进行过重裱,康熙乙酉年为康熙四十四年,距西征仅十二年,而后一次重裱(嘉庆二十年)则距第一次重裱相差一百一十年。由此推断,康熙不可能赏赐一堂破损的水陆画于地方,而赏赐之物,当妥为保管,也不可能在十二年之内就需要重裱。康熙乙酉重裱题记云∶“恒城自驻防以来,凡寺宇古刹处处涣然,而宝宁寺尤为美备,寺中相传有敕赐镇边水陆一堂,妙相庄严,非寻常笔迹所同,但历年已久。而香烛薰绕,金彩每多尘蔽,主持广居立志重新,已非一日……”“相传”说明在重裱时,此画已属相传,不属于记忆中的范畴了,“历年已久”,究竟有多久,不能确定,但绝非十二年之久的!因此只能说明敕赐镇边水陆画应为康熙之前来到右玉的,而康熙赏赐说亦仅为传说而已,不足为凭。
嘉靖赏赐说。明嘉靖年间,边乱不断,蒙古鞑靶部头领俺答之子辛爱的小老婆桃松寨,因奸情被丈夫发现后逃到大同,被宣大总督杨顺送到京城邀功请赏。俺答以此为由,又一次发动了对明朝的战争,而战争的桥头堡则为边关要冲杀胡(虎)口及重镇右玉林卫(右卫城)。俺答攻破杀胡口后直达右玉林卫。右玉林卫是守卫边墙的重镇,但孤悬边塞,兵少粮缺,然英勇尚武的右卫军民并不畏敌,浴血奋战,多次打退了攻城的敌军。但自己也伤亡较大,守将王德牺牲。有一位居家养病的将军尚表勇挑重担,行伍出身的麻家父子“倡义效死、倾困赈旅”,“军民士气不变,悉力捍御”,给鞑以沉重的打击,然敌军将右卫城包围了好几层,时间从嘉靖三十六年农历九月至第二年农历四月,达八个月之久,城里已是柴断粮绝,饿孬遍地,岌岌可危。
右玉林卫被困的消息传达京城后,明廷专门讨论救援之事。以奸相严嵩为首的妥协派,认为右卫城地处边塞,干脆弃之不用,而主战派力陈利害,嘉靖才派兵救援。鞑军闻听明朝大军到来,又久战不胜,慌撤围而去。此时城内军民已奄奄一息,援军入城后才得以救济。
战后杨博暂留大同,整饬边防及军务,“修筑宣大边墙千余里”“筑堡寨九座”,修“烽墩二千八百有余”,使边防得到了加强。但并未出现赏赐水陆画之事,况嘉靖深居幽宫,沉溺于老道炼丹之术,对佛事似乎并不感兴趣;从人性上讲,嘉靖寡恩薄义,不理朝政,视大臣如蝼蚁,稍有不顺即廷杖处死,更何况是远在边界的右玉军民呢岂有赏边水陆画,追亡将士之魂哉?
英宗赏赐说。明英宗时,蒙古瓦刺部逐渐强盛起来,又统一了蒙古,控制了东起辽河,西至阴山东麓的大片土地,不断挑起战端。明正统十四年(年)农历七月,瓦刺头领也先兵分四路向明朝沿边大举进犯。也先亲率主力向大同一带进军。大同守军北上抵抗,明军失利,参将吴浩身亡,在阳高一带再战,又败,守将宗英、朱冕战死,大同守备郭敬(太监)躲在草丛中幸免一死。
也先寇边及明军战败的消息传到京城后,朝廷急商对策。当时专权的太监王振想利用这次机会狐假虎威,炫耀自己的权势,竭力主张皇帝亲征。于是皇帝朱祁镇不顾众大臣的反对,贸然统率五十万大军亲征。从北京、宣府浩浩荡荡向大同进发。八月到达大同,正赶上连日霾雨,士气不振。但皇帝昏聩、太监昏庸,不懂战术、不恤下情,更使军心涣散。王振以为五十万大军来吓一吓,瓦刺就会退军,但听到同党郭敬把战况一说,吓得魂飞魄散,又极力劝说皇帝回师返京。结果五十万大军只在大同停留了三天,未与敌军交战就离去。
八月中旬明军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西),与瓦剌军交战失利,明军死伤数十万,骡马损失二十万头,辎重无法计算,文武大臣战死五十多人,王振死于乱军,皇帝朱祁镇被俘。
也先挟持朱祁镇至大同“索金币”,宣大“都督郭登予金三万,也先遂挟帝北行”。后也先又带着朱祁镇多次到大同索金,郭登两次设计袭击瓦刺军,夺取皇帝,惜未成功。其后,也先以送还朱祁镇为名,进攻北京。这时明朝已在主战派于谦的主持下,另立新帝朱祁钰,改号景泰元年(年),杀死王振同党,调集兵马,募兵抗战。也先阴谋没有得逞,又北行而去。过了一段时间,也先认为拘留一个废帝没有多大用处,杀死又会与明朝结下大仇,不如放回。明英宗结束一年的囚徒生活,回到北京,被尊为太上皇。
据《朔平府志》记载∶"景泰元年八月初三日,北也先等设宴饯送英宗于道,下马解弓战裾以进,诸将帅皆罗拜而去。伯颜帖木儿独送至野狐岭,进酒帐。既毕,众皆道旁送驾,进牛羊。奉迎使杨善呼曰‘皇帝行矣。’伯颜帖木儿送出野狐岭,英宗揽辔慰藉,与之别。”
究竟英宗被俘一年来,囚于何处史书没有记载,《明史》云∶英宗“北狩”。“北狩”只是史书隐晦的说法,显然“北狩”即是被俘、被囚。随着岁月的风蚀剥去历史的尘埃,有些历史谜团正逐渐被人们解开∶英宗当年很可能被囚于右玉林卫(右卫城)宝宁寺之地。
宝宁寺原有《敕赐宝宁寺记》碑一通,碑文如下∶
大同西路右卫城宝宁寺于景泰乙亥请勒、天顺庚辰盖造。碑文既携,但未果立。成化甲午秋,予固提督边储来城邸,于寺见碑仆地,询诸位持僧。清晓云∶“是碑唐勒□十五载矣,恒欲立之,微倡帅者。”予恐湮其前绩,俾本僧绘图眷文,道其始末。禀诸予∶钦差分守大同西路御马监太监常正、钦差游击将军后军囗囗府囗督金事囗谦、钦差分守大同西路右参将都指挥使李镐。□日是亦胜口口宜口口遂命口口筑此于正口前口口口囗命石工修琢囗囗囗□□高囗合,择吉建立,以垂不朽。予故庸书,以此记岁月云旨。
大明成化十年秋月吉旦,承事郎大同府通判淮南曹囗书。
从该碑文字我们知道宝宁寺于景泰六年(年)奉旨建造,天顺四年(年)竣工,工期六年,建寺石碑镌刻已十五载放在地上没有立起来,恰遇钦差分守大同西路御马监太监常正来到该寺,弥补了此件憾事。但建寺的正碑(及碑文)没有遗存下来,从而使我们无法更清楚地了解建寺的情况。然该文也给我们两点史实∶一是宝宁寺乃奉旨建造二是景泰六年奠基,天顺四年竣工,工期六年,明朝两任皇帝都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wh/32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