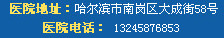“生活”的意思人人都清楚,就是人们为了生存下去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包括衣食住行、工作、婚姻等多个方面,而这里的“场景”,我们可以将其拆字理解为场所和景观,也就是诗僧身处其间的生活环境。场景又有自然和社会之分,因此这里的“生活场景”的定义是指诗僧的日常生活状态和他们的居处环境。
这里的禅院只是一个概略的说法,强调的是诗僧们起居的院落,也就是他们的居宅,但为了表明他们僧侣的身份,与俗世有所区别,姑且称之为禅院。下面会先介绍一下唐代诗僧的诗作中反映出的禅院的类型,再来谈诗僧如何利用植物营造禅院环境。
一、唐代诗僧的生活场景
1.唐代诗僧的日常活动
我们讨论的诗僧群体仅仅是唐代僧侣中很小的一部分,他们的生活与普通的僧人是有所不同的。我们从唐诗中找出的线索表明,诗僧的生活并非严格的教徒式的,而是晕染上了诗人的色彩,与当时唐代的文人生活方式有相同之处。
我们将诗僧的诗歌与学界各种研究僧人生活的专著中的相关内容相互映照,发现诗僧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宗教课业,这包括坐禅、诵经与写经,放生,游方和交接。交接就是交往和接待,是社交活动的代称。
2.唐代诗僧的居处环境
诗僧的居住环境有小环境与大环境之分,小环境指的是寺院僧房,大环境指的是寺院所处的山林或江边、湖边等地方。比如寒山和尚隐居的天台山就是大环境的代表,但僧人的具体居住并不限于某寺或某禅院,也有不少人单辟住所的,还有人依旧居于俗家。
郝春文曾研究过敦煌僧尼的生活方式并将其分为两大类,一是住在寺外的散众,一是住在寺内的僧尼。“敦煌的住家僧尼和其他僧尼一样经过了寺院为他们举行的出家、受戒仪式”,“住家僧尼虽然吃、住在家中,但也要参加寺院组织的法事活动,并获得宗教收入”。
当然敦煌僧尼的情况有其特殊性,我们通读过唐代诗僧的作品后,发现没有证据表明有诗僧在俗家居住的。寒山和尚虽然有时会想起妻子,“昨夜梦还家,见妇机中织”,但他出家后一直居于天台没有再回过俗家。
唐代诗僧中有的僧人有开辟草堂与营建别墅的风气。如齐己有诗《夏日草堂作》、《西墅新居》、《独院偶作》,贯休有诗《湖头别墅三首》。另外,处默有诗《忆庐山旧居》,齐己有诗《移居》,说明有些诗僧还时常更换住处。
至于寺院内的建筑小格局,各个时代的诗僧所居不尽相同,但大致体式相差不多。张十庆总结禅寺殿堂寮舍形制有:佛殿、法堂与方丈,僧堂、众寮与库院,山门与回廊,东司与宣明,伽蓝堂与祖师堂,钟楼与藏殿,水陆堂及其它。
陈大为将敦煌的寺院建筑分为钟楼、经楼、大殿、讲堂、厨舍、仓库、其他堂(七佛堂、众堂、暖堂、观音堂等)和院落八大类。“寺院建筑的总体布局一般有东西两座角楼,悬钟一口地为钟楼,满贮经卷的为经楼”;
“讲堂系佛寺里讲经说法之建筑”;“讲堂一般建于寺院的后面”;“敦煌寺院的厨舍分为两种,一种是寺院的公共厨舍,为所有僧人服务;一种是僧人个人的厨舍,系僧人自己使用”;“敦煌诸寺都有自己的仓库”。
由此可知,唐代诗僧在寺内所居大抵有三处,一是修课业之所,即讲堂、说法堂等,二是用斋饭之所,即厨房,三是休憩睡眠之所,即僧寮宿舍。至于经楼或藏经阁,相当于寺内的图书馆,可归之于修课业之所。另外,陈大为还指出,在敦煌的寺院中,“享有院子的大多为僧官及身份较高的僧人”。
通过上文的简要论述,我们已大致了解了诗僧群体的日常生活场景。总结起来说,唐代诗僧的日常生活状态是:诗僧们生活在大自然(山林、水泽之间)与小自然(禅院)当中,在此课业、禅修,并进行诗歌创作。
二、诗僧利用植物在禅院中建构自然
唐代诗僧的诗中提到的禅院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平常自己居住的,一是借宿其他人、其他寺庙的,如果用较为精炼的词来概括,可以表述为吾家和别宅。王梵志的诗中多次提到“吾宅”和“我家”,比如“吾宅在丘荒,园林出松柏。邻接千年塚,故路来长陌”,“我家在何处结宇对山阿。院侧狐狸窟,门前乌鹊窠”。
还有一些诗章专门描述了自己的居所,比如寒山的诗中有很多这样的表述,例如“三界横眠闲无事,明月清风是我家”,“桂栋非吾宅,松林是我家”,“我家本住在寒山,石岩栖息离烦缘”,他也有诗专门描述居宅,“寒山有一宅,宅中无阑隔。六门左右通,堂中见天碧。房房虚索索,东壁打西壁”。
诗僧除了住在寺院,还有自建屋舍居住的,比如皎然《湖南草堂读书招李少府》、释泚《北原别业》、贯休《湖头别墅》、齐己《西墅新居》、《夏曰草堂作》等诗,都是这种现象的反映。
诗僧们即使移出寺外居住,也是不涉尘俗的。贯休《湖头别墅》三首之二说“更无他事出,只有衲僧来”,说明他们还是多与僧侣打交道,反映出诗僧们如同隐士一般的生活。但是隐居的士人往往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而僧人则只追求自己的“道心”,写出的诗也必以斯心为旨归,所谓“吟非俗肺肠”“禅外求诗妙”是也。
寄宿别宅的情况较为复杂,有住别的寺庙的,如无可《宿西岳白石院》、皎然《宿吴匡山破寺》、泠然《宿九华化成寺庄》、栖蟾《再宿京口禅院》等。有住在交好者家中的,如清江《宿严秘书宅》、无可《暮秋宿友人居》、齐己《宿舒湖希上人房》、罢域《宿郑谏议山居》等。
还有住在驿站的,如灵一《同使君宿大梁驿》,清江《喜皇甫大夫同宿大梁驿》等。还有住在道观的,如皎然《宿道士观》、贯休《宿赤松山观题道人水阁兼寄郡守》、齐己《宿简寂观》等。另外还有住在野外乡村的,如贯休《宿深村》、贯休《春晚书山家屋壁》二首之二“山翁留我宿又宿”等。
禅院之于诗僧的意义,首先在于从物质上保证了诗僧的安定生活。杜甫在茅屋被秋风吹破之后呜呼哀叹,是因为止栖之所的不稳固使得心情烦躁,而诗僧们因为归宿之地的安定,心也安定了。怀浦《赠智舟三藏》云“壮岁心难伏,师心伏岂难。寻常独在院,行坐不离坛”,超然物外的独立小院造就了诗僧的独立禅心。
禅院之于诗僧的意义还在于从精神上建构了诗僧的小天地。诗僧们在小院中修习禅法,“长期生活在内心世界中”,“不再向自身之外去寻求幸福、理解和智慧”。皎然《答孟秀才》云“羸疾依小院,空闲趣自深”。这一深趣是由诗僧冥想出来的,是精神层面的趣味,平民白丁的小院中就不会产生此种深趣。
屋舍院落都是人建造的,而人是有对美的追求的,尤其是诗人,他们不会满足于片瓦遮身,而会用心去营造属于自己的院落,使之符合自己的美学品味。笔者认为诗僧的美学品味就是自然之美。有学者注意到整个中晚唐的士人大抵都有倾心自然的一面,这与诗人们在精神上向佛禅皈依有关。
“晚唐士人……如果没有佛教,他们的心理实际上是很难平衡的……他们审美的视点己不在社会,而在自然,或者说在心境更为恰切。”“一方面是佛门,一方面是大自然,遂使原本胸怀磊落、慷慨有奇志的诗人在这不得意的境遇中安定了自己的心性。”
如果我们将诗僧与中晚唐士人统而论之,他们都是与自然为伴的人,但诗僧更少世俗、官场、情爱等尘网中的烦心事,诗僧比之士人最大限度地做到了“大丈夫儿合自由”,他们可以心无旁骛地求佛理、念禅心,将自己整个儿地投入自然之中。
比如贯休,他在山野里建造属于自己的禅院,他开门便可见到山水,因而无须刻意营造。但如果筑室于人群之中,无法与自然亲密接触,就只好别做他法,将自然请进院落,也就是在自己的院里重塑一个自然天地。
便于栽种和管理的植物是诗僧建构人造自然的重要依凭之物。齐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他尽心尽力地在庭院之中再造自然,齐己利用主要有松、竹、柳、苔、莲、莎草、藤萝等植物,费心劳神地仔细布置自己的禅院环境,希望能够从松风竹韵之中寻得自然的妙处。
尤其《谢主人石笋》一诗说得最为直白,齐己非常感谢别人送给自己的石笋,他把石笋安放在竹林里花丛边,这就增加了一份幽静之感,有了院里的人造自然,他心满意足地感叹道:“从此以后我可以经常围绕着石笋点缀的竹林吟诗了,这消除了我归向高山的意图。”
他在《假山》一诗的序中说:“假山者,盖怀匡庐有作也。往岁尝居东郭,因梦觉,遂图于壁。迄于十秋,而攒青叠碧于寤寐间,宛若扪萝挽树而升彼绝顶,今所作倣像一面,故不尽万壑千岩神仙鬼怪之宅。聊得解怀,既而功就,乃激幽抱,而作是诗,终于一百八十言尔。”
所谓“攒青叠碧”“扪萝挽树”,也就是在假山四周栽植各类花木,以此仿造出自然山川的面貌,可见在齐己的心目中,这个庭院中的假山己成为小匡庐,而当他“解怀”之后写下诗篇时,自然就被诗意地留存在纸笔之间了。
三、总结
在本章中,我们运用一些诗歌做例证,论证了唐代诗僧群体对自然山水有追慕向往之情,对自然界中的花草树木有喜爱之意。正因为这种情意,诗僧们热衷于在诗歌中书写自然、书写植物,他们通过书写山水和植物来记录日常生活中的诗思禅念。
他们非常自觉地做着与诗和僧这双重身份相应的事,也写下与诗和僧这双重身份相应的诗,他们始终有“禅子有情非世情”的清醒认识。他们虽然有世俗化的一面,在日常行事与诗歌艺术上也表现出向文人靠拢的倾向,但他们终究不是以进仕朝廷为人生理想的士大夫文人,在诸多方面依然维持了自身的特色。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hl/47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