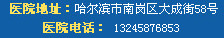相思或许不老,爱情的香气或许永恒,人却终会白头。即使牵着她的手一起走到白头,也终究只能独自一人走到终点。生老病死,是一个人的事,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爱情,只能是爱情,不可能成为人生的全部。而白石的人生里,除去爱情,还有更多需要他一力承担的事,比如生计、才华、功名事,比如师友情、故友情、挚友情。
苏轼贬谪黄州时,好友章质夫曾作《水龙吟》词吟咏杨花,名动一时。苏轼极爱此词,便和韵一曲,开篇道:“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仅此一句,神韵已全出。王国维评苏轼咏杨花词,说它分明只是一首和韵之作,却胜过原词数倍,于是感叹才情不可强求。作词一事,于苏轼不过是小技,却因才情在身,将小技做出了大文章。
白石亦是才情满身,诗词文章,音律书法,无一不通,且雅善古琴箫笛,文友宾客会集的歌舞酒筵之上,自创新曲,慢拨琴弦,临风吹奏一支悠长箫曲,于他也只是小技。但白石的小技里,何尝没有大文章。
所谓才情,不应只是技艺的娴熟,更是与丰富的心灵世界融为一体的某种东西,是一个人身上的气场和天性。常想,那些高官厚禄在身的人,为何如此青睐白石。固然是欣赏他的品格、惊艳于他的才华,却也未必不是因为与他相处,总能体验惊喜,永不会感觉乏味。而白石给人的惊喜,并非奏琴吹箫的技巧有多么高超,并非他总能临场编曲作词,顷刻挥就,当是他每一次吹奏,都独一无二,情怀自有深浅,情趣自有高下;每一次编作,都是心灵世界的映现,总能造就一曲曲妙不可言、不可复制、不再重现的词作。
惟其如此,这位江湖困顿终生的文士,心灵里的那一方宇宙,才让如此多功成名就之人向往之、激赏之,拼力护之周全。
白石此生,便如陈藏一所言,“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客”,漫长的漂泊生涯中,他从来都清贫如洗,也从来不曾缺衣少食。当他在湖州定居近十年之后,一直扶持他的萧德藻终因年事已高,被子侄接走,离开了湖州。白石虽在湖州失了依傍,却得以在好友张鉴的帮助下,于庆元二年(年)举家迁往杭州,从此依张鉴居于杭州东青门附近。
《姜尧章自叙》一文末尾处,白石提及张鉴,说了一段情意深挚的话:
嗟乎!四海之内,知己者不为少矣,而未有能振之于窭困无聊之地者。旧所依倚,惟张兄平甫,其人甚贤。十年相处,情甚骨肉。而某亦竭诚尽力,忧乐同念。平甫念其困踬场屋,至欲输资以拜爵,某辞谢不愿,又欲割锡山之膏腴以养其山林无用之身。惜乎平甫下世,今惘惘然若有所失。人生百年有几,宾主如某与平甫者复有几?抚事感慨,不能为怀。
“平甫”即张鉴。他是南宋大将张俊之孙,世家贵胄,家产丰厚,对白石生活上的资助不可谓不大。而张鉴去世后,白石心中深切的怀念和感激之情,却与此无关。他感激的不是张鉴愿意为他买官拜爵,愿意给他衣食无忧的宽裕生活,而是此番举动背后的挚情。他怀念的不是友人的贤善和慷慨,却是“宾主如某与平甫者有几”,人生匆匆百年,自己竟能得友如此,得主如此,实在难得。
纳交于张鉴,与白石当初识交萧德藻不同。萧氏与白石之父姜噩同为绍兴三十年(年)进士,有同期之谊,故而他对白石的赏识、提拔,是长辈情谊,是护犊之情。张鉴与白石却为平辈,二人之情,纯是友人之间的惺惺相惜。
他们惺惺相惜得如此坦然厚重,以至于“十年相处,情甚骨肉”。若论身份,张鉴是主,白石是宾,若论交情,却是知音,是至交,是不分彼此的血亲之情。白石不接受张鉴白白送给他的名利,何尝不是为了保护这份重于骨肉的情谊。
彼时,张鉴和白石心底,定是有着相同的回响:人生得此挚友,夫复何求。
“抚事感慨,不能为怀”的白石,若见了自己此前与张鉴携手共赏好景时写下的记游词,不知会怎样掩卷长叹。
十亩梅花作雪飞,冷香下、携手多时。两年不到断桥西,长笛为予吹。
人妒垂杨绿,春风为染作仙衣。垂杨却又妒腰肢,近前舞丝丝。
——姜夔《莺声绕红楼》
写这首《莺声绕红楼》时,白石还未移家杭州,从孤身客居的绍兴赴杭州,只为与张鉴携手游湖赏梅。
大千世界,从来不缺美景,可是,任是再好的良辰好景,赏心乐事,总须有人共度、共赏、共品,否则也不过空付与时光深处的断井颓垣。白石是行过无数路,历遍了好景的人,而能进入他词章的地名,也不过那么几个。只因孤身一人赏过的风景,并不能刻骨铭心。多少人穷尽才笔、费尽笔墨咏赞西湖之美,在白石眼底,这一方明净湖水的风姿,却只因佳人、胜友在侧,才足够旖旎妖娆。
宋初高士林逋曾在西湖河畔的孤山隐居,以种梅为乐,故而孤山上有“十亩梅花作雪飞”的胜景。白石与好友于幽冷芳香中携手徜徉,见梅花在风中如雪飘扬,真不知是何等迷醉之佳境。
以张鉴之身家,游湖自与寻常人不同,非大手笔不能尽享其乐。他是携了家妓、乐工,浩浩荡荡前来,是要为白石尽地主之谊,亦是一个富家公子倾其所有款待挚友的情意。乐工是国工,技艺高超,家妓为应西湖杨柳之景,皆以柳黄为衣,雅致不俗,可见张鉴不是空有一身富贵习气的纨绔子弟,他有奢靡、挥霍的资本,却也有足以与白石相匹的精致品位和高雅情趣。
白石自是领情。
“长笛为予吹”,是感激,也是得意了。为什么不可以得意?他两年未到断桥,如今重游,却有国工为他吹笛,歌姬舞女为他助兴,更有挚友在畔,言谈欢笑,他得意得名正言顺,心安理得。
所以他见西湖“绿杨阴里白沙堤”(白居易《钱塘湖春行》)的胜景,蓦然间福至心灵,在词中写下神来一笔:分不清是人妒垂杨绿,才将它的姿色夺来制成衣裙,仿若春风染过的颜色,衬得佳人肌肤胜雪,眉目如烟,还是垂杨嫉妒人的细软腰肢,才会在春风里长条起舞,搔首弄姿,直欲胜过佳人的娇美风采和轻盈舞腰。
绿衣红颜,舞姿翩翩,白堤青柳,丝丝摇漾,这西湖岸边的游乐盛事,当真醉人心魂,不知要用怎样美妙的文字来言说,方可拈出其中好处。而白石不过悠悠道来,丝毫不见锻炼之力、斧凿之痕,却已将乐妓之美、绿杨之美道尽,更有两相映衬、美不胜收之妙。
佳时胜境,人与时日、风景全然相契,这样的片刻在人的一生中并不多见。此时的白石却体会到了,身与心至,神与魂合,笔随意动,完美得严丝合缝,文字仿佛直接从笔端流出,又仿佛早已天成,只需信手拈来,便如梦中偶得,得来全不费工夫。
只是,如此乐事,比照此前他在绍兴的孤灯苦影,飘零滋味,显得有些不真实,教人平白生出“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茫然和困惑,然而困惑里也有满足,仍是不真实的,像脚踩棉花地,醺醺然的,仿佛是有些醉了,怕眼前一切皆是醉里景象,顷刻便醒,又怕它如短暂一梦,做不到头,天就亮了。
后来,当白石隔着生死的界线回望绍熙五年(年)那一场游湖盛事,才知那确实是一场梦,是张鉴给予他的一场靡梦,醉人,可是也灼人。那时,他以绝妙词笔记下人生盛景,待友人西去,这盛景便成了一杯苦酒,一道冷茶,一曲总也唱不完的哀歌。
然而哀歌也是歌。既是歌,便有情意在。当年面对好友的盛情,他作《莺声绕红楼》,是繁华里一曲高歌,倾尽才情以报,日后待他重新吟唱这首曲词,亦是衰瑟里一曲悲吟,倾尽深情去悼怀思念。他是倾尽了此生欢娱和悲哀,寄君一曲,托付衷肠事。待此曲终了,便无须再论聚散,因为终有一日,他将与所有告别过的人在另一个世界欣喜重逢。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hl/2314.html